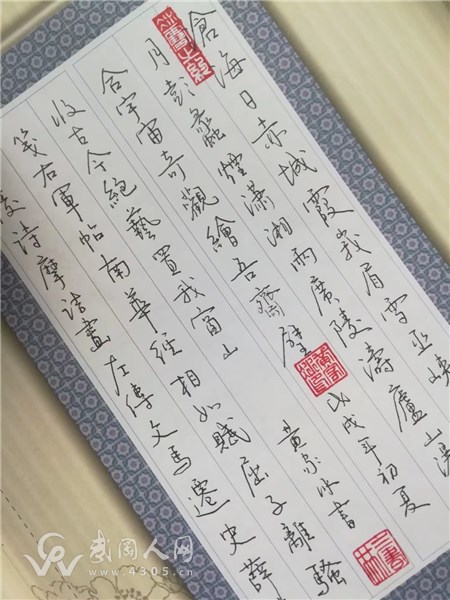椏(讀音同:阿)扎話
都梁記憶∕文
以發(fā)源于新寧縣的那支水為標準����,武岡南鄉(xiāng)安心觀上去五里�����,叫長鋪里�����。長鋪里分為街上�����,周家鄧家王家�。我的外婆家就是長鋪里周家��。

長鋪里����,通常指長鋪里街上。周家王家鄧家��,離長鋪街上還有一里路����。三個村落像眾星捧月拱護著長鋪街上���!
從小到現(xiàn)在去舅舅家,沒有覺出周家與街上有什么區(qū)別�����。讀初中時�,聽班主任兼語文老師的蕭孝和老師說了一句安心觀的俗語,“長鋪里的釘心話�����,周家人的椏扎話����。”一直縈繞腦際����。 就覺得周家與五百米遠的長鋪街上,像兩個性格迥異的故人�����,深深地嵌入到了深遠記憶中�����。
蕭老師是武岡城郊南門外資南村人�����,他當我們初中班主任之前在安心觀教過高中的�。所以比我大十三四歲的蕭老師知道好多安心觀俗語與掌故。從那個時候起���,釘心話和椏扎話的概念����,就一直影響著我對長鋪周家與長鋪街上的認識��!
釘心話�,也稱傷心話,就是不顧情面的話��。什么人對什么人敢不講情面��?什么人對什么人必須講情面���?這些問題很多時候跟勢力有關系��!而勢力���,分財勢和人勢��。
椏扎話這個概念���,許多年來,也只是聽說���。到底能不能用這三個字來表達�����?不確定�����。
四十年來����, 蕭老師說的周家人椏扎話故事���,歷歷在目:
武岡�����、新寧�����、城步�,三縣交界之地叫照面山��。照面山峰頂可是比云山寶頂還要高���。從長鋪周家村子后面爬照面山���,翻越照面山可以從武岡的安心觀到達城步或者新寧地界。照面山有一座山峰���,可以“一腳能踏三縣���!”如果登云山需要兩個小時,那么登照面山可能要三個小時�����?
一天,有個外地人孤孤單單走照面山��,累且無聊中�����,見前面一挑夫負重踽踽獨行���。立時興起�,三步并作兩步追上�,搭訕道:
“老兄哪里人?”
“長鋪周家���?��!碧舴驓獯瓏u噓地答。
“久聞周家人椏扎話出名�����,港一句來聽��?”
“好啊�!替我挑著,港給你聽�!”挑夫表面不慍不惱。
外地人無言以對�,尷尬之極。
這就是流傳至今的“周家椏扎話”故事�。

椏扎話比較起釘心話來,同樣是心里有氣���,但氣卻以不同方式泄出來:釘心話剛性,椏扎話綿軟�!椏扎話就像一根長在樹椏里的刺,扎上你�����,讓你辦不開取不下���,得慢慢來�����。被樹椏里的刺扎上�,往往是自找的,有苦說不出�。
聽說外公兄弟很多。外公生下兩個舅舅�,大舅舅在改朝換代戰(zhàn)爭時被抓壯丁。當時是要抓一位堂舅舅的�,因為是“三抽一”規(guī)矩。但堂舅舅的父親使了錢���,才抓了大舅舅去的���。堂舅舅的父親與客公是親六兄弟之一,之后大舅舅再也沒有回來�,所以在父親手里堂客公堂舅舅就不來往的。外婆也從此神經(jīng)失常�����,痛失兒子的外婆每天長歌當哭一般唱著同一句話����,“哪曾雞叫哪曾光?鑰匙不到鎖不開���!”外婆是在等不到大舅這把鑰匙含恨離世的��。外婆離世之時����,根本沒有顧及身后還有冇長大成人的我娘!
細舅舅比我娘大��。外婆死后外公家遭過一場大火�,燒光了所有家當?����!百\過挑一擔火過得一看���!這是安心觀的老話,是娘說給我聽的�����。
三縣交界的照面山腳下是長鋪周家��,所以娘說的許多強盜打搶的故事�����,讓我總覺得周家總是云霧籠罩下的樣子。村子里的人好像很少見陽光�,像樹蔭下生長的草木?這種感覺怎么來的��?是娘說故事的影響��?還是看到舅舅他們的身材面貌�?說不清!
記憶里����,跟父親沒有去過幾次舅舅家,舅舅的溫軟懦弱讓父親半點看不起����。舅舅一共有兩個兒子四個女兒,舅舅只有活到四十歲���。因為父親比娘大九歲���,所以舅舅比父親小。年齡小膽子小的舅舅有年快過年的時候�����,去武岡城里辦年貨,早晨從家里去的時候要經(jīng)過我家���。剛好那天我家殺年豬��,趕得早不如趕得巧���!娘見舅舅體弱多病孩子又多,心想要舅舅下午從城里轉來時進屋����。但因為父親早晨說了舅舅幾句“恨鐵不成鋼”的話,娘等到天黑�,也沒有等到舅舅進屋來!舅舅直接從武岡城里回家去了��。那個時候鄉(xiāng)下人進城�,如果說我們進城是三十里路,那么舅舅進城應該有四十五里����?來回就是九十里�����。舅舅體質之瘦弱在我的眼里,算骨骼之清奇�!以至于后來讀《菜根譚》里那句“志以淡泊明節(jié)從肥甘喪”的經(jīng)典古訓時,就想到我舅舅���。
舅舅的瘦與所有堂舅舅們的瘦�,皮膚的白凈�����,我苦苦思索了到了現(xiàn)在五十歲���,應該是有統(tǒng)一緣由的�?
娘說過:不管春夏秋冬寒山雪溝�����,到長鋪周家去�,看到抄紙佬頭纏長汗巾,光著腳�,一腳一哼踩料的情景,十有八九會感嘆��,“這人霸蠻��,這么重病包著頭還打赤腳干活?”其實����,這是長鋪周家人正常的生息勞作。

千古以來�����,靠山吃山的長鋪周家人��,什么時候以照面山的楠竹為原料手工造紙����,沒有考究, 一直以來只有 從娘說的故事里約略知道:
每到谷雨前后��,周家的男人們頭纏包頭�����,手握鋒利的矛利刀���,不避晴雨��,上山把開葉不久的新竹砍倒�,撂段�����,一分為四破成片��,堆碼在凼里�。然后一層竹料灑一層石灰,堰上水�����。假以時日�����,堿性的石灰水就將竹片腐蝕成絲狀叫”麻絲“的造紙原料����。再從凼里撈出來,曬干����。農(nóng)閑時光一擔一擔挑回家,再用水浸泡脹發(fā)。外公家舅舅們”哼幾哼幾“�,就在塹有條紋的石板上跺腳,將重新泡軟的麻絲跺成紙漿����。
在長鋪周家,麻絲就是這樣被肉體凡胎的舅舅們用腳板搗成紙漿的�。
寒風凜冽的天氣里,紙漿好了的時候水也熱了�����,人也熱了���。然后把紙漿撈進紙槽���,加水稀釋;再把粗纖維弄出來�,最后一簾一簾撈起紙漿成片;上榨�����,下榨�����;批紙,晾曬���;最后收紙打包。抄紙的每一道工藝在舅舅們的手里都那么細心精致���!為保證紙張烘曬時好批���,撈漿成紙的工藝中,專門用一種樹葉熬成叫滑汁的東西孱到里面���。否則成跺的濕紙不好批��,或者批不開�?
手工抄紙�,與后來的機械造紙概念不同的地方很多。機械造紙叫造����,外公家造紙叫抄。抄與造又不同��,抄是雙手都要配合的動作。

那個時候����,武岡城里做鞭炮,也是用舅舅他們造的紙做原料�。鞭炮制作工藝之繁雜聽說是有一百零八道?其中大部分包括從竹子到紙張的過程��。
如果說我們的祖宗通常以耕織傳家�,那么說外公他們則是耕抄傳家了!一年四季��,土地的耕作是體力活�����,砍料抄紙更是體力活���。一年三百六十天��,他們沒有幾天不出汗���,頻繁出汗的男人,跟女人一樣�����,女人一個月一次新陳代謝,而這種男人每天都在新陳代謝���。所以舅舅們皮膚白皙���,骨骼清奇�����;舅舅們沒有脾氣的性格如女人一樣��,也許跟每天不留余地的勞作有關系�����?
千百年來���,所謂街上者��,皆人杰地靈之所��!常常以聰明狡詐的生意人集聚的地方叫街上�。 他們左店右鋪博弈,不用力氣只用腦�,常常眼明手快臉黑肚肥。也許這就是街上人”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“的根源����?
我二姑爺就在長鋪街上,二姑爺是祖?zhèn)魃馊?����,他家開過槽房賣過肉���。他賣肉的脾氣聽父親說過:
一般人到二姑爺?shù)娜獍盖百I肉���,不要提要求。只要一張口�����,二姑爺就眼睛瞪得銅鈴大�����,惡狠狠一句��,”你是吃肉的王!“所以二姑爺?shù)臍⒇i生意�,在長鋪里是出了名的狠。
二姑爺吹胡子瞪眼的樣子我記憶猶新�。二姑爺和二姑媽只生個一個表姐,沒有兒子�。后來抱養(yǎng)一個兒子,兒子生了一孫子兩孫女后�,在公社煤礦井下放炮炸死,二姑爺?shù)南掳肷桥稣疹櫟?。女婿當過兵,在縣二輕局工作����,女婿比女兒大很多一樣��?
二姑爺抱養(yǎng)的兒子我叫表哥�。表哥勤勞扎實,表嫂性格笨拙��。表哥不在的時候�,二姑爺還是不太把表嫂當人看。
有一年冬天����,快過年的時候��,生產(chǎn)隊干了魚塘�����,爹要我放學后去二姑媽家送一個半臘的草魚�。那魚也就是兩斤多的樣子���。走了十多里路到二姑媽家�,天快黑了����,我被留宿。晚飯的時候���,那個時候一般人沒有晚飯吃���。晚飯的菜就弄了我送去的魚的魚頭,風臘的魚頭看不到半點肉�����。微弱的煤油燈下二姑爺在喝酒。我盡管沒有十歲�����,但我是客人��,在姑媽的眼中�,父親是最有能力的娘家兄弟。我坐在冬天的灶臺靠墻的角落��,是最尊貴的位置���。表嫂站著吃飯��,時不時從人縫里伸筷子進來夾一筷菜�。當表嫂一轉身把沒有半點肉的魚骨頭扔到地上的時候�,被二姑爺看到了��,半點不留情面地叫��,”咸水呢冇津卦就丟�,大富大貴了?“當時的二姑爺已經(jīng)很老了�����,我清楚地記得他烏黑的手爪抓著沒有半點肉的魚骨細心地吸吮。
不久前跟大姐說起這些過節(jié)時����,大姐說,”要是表嫂在哪碗肉菜里多夾一回����,他就要鼓起眼睛哼一聲,“在咯碗里倒起卦了�����!”意思是:筷子在這碗里迷路了���!
祖宗傳下來的規(guī)矩�,哼不亂哼的�。哼久成咒,咒久成蠱的�!大概哼與恨諧音吧?
唉����!天生是冇得崽的命。
千百年來,到底生崽生女跟殺豬有沒有關系��?現(xiàn)在長鋪街上也有一個殺豬的��,也是二姑爺一樣的遭遇�����。通常的解釋是殺豬人作了孽�����,其實應該解釋為殺豬經(jīng)常吃肉的后果��。經(jīng)常吃肉的人與經(jīng)常粗茶淡飯的人相比����,體液酸堿度不同的,生育條件也自然不同���。
相對來說���,不干體力活的長鋪街上人集聚的身體能量大���,火氣也猛�。所以看不慣別人就說“脹眼睛”。脹眼睛了就會罵釘心話�,不罵了釘心話,心理生理不平衡的��。
經(jīng)常干體力活的長鋪周家人��,沒有火氣跟人計較�����,有想法也醇和得多�。椏扎話,是沒有火氣的周家人遇上敢說釘心話的街上人�����,偃旗息鼓甘拜下風的心情����。像照面山的云霧:云隨風走,霧怕陽光���。
年復一年�,累死累活的周家人賣了紙,賺到的錢一般在長鋪街上消費掉����!滋養(yǎng)著街上人的臉黑心毒!
舅舅早已不在���,舅舅家后面的山道��,也是難得一見的槽路����。
多少年來��,是上山下山的周家人放牛拖柴�,腳印蹄踩,踐踏出來的�����?��?巢袢送前巡駬讣缟?���,尾部在地上�,拖著下山。拖柴下山的周家人����,比挑柴下山,輕松多了���。周家人在靠山吃山的歲月里����,照面山給了他們艱辛的同時��,也給了他們滋養(yǎng)���。年深日久��,山道的泥翻出來了�����,石頭也出來了�����。水洗柴掛�����,翻出來的泥石順坡順水而去���。周而復始�����,舅舅家后面的槽路就形成了�����。
照面山�����,是一位寬厚仁慈母親�����。滋養(yǎng)過勤勞富庶��,也頤養(yǎng)著罪惡貧窮���。匪患猖獗是照面山善良背 后的隱痛��!

多少年來�����,土匪只要搶了長鋪周家,眨眼工夫���,就會悠游于照面山茫茫密林之中����,讓官府也望山興嘆�����。在這里���,土匪是什么���?也是一方水土的特產(chǎn)!
上個世紀改朝換代的前夜����,那個時候長鋪里還屬新寧縣管�����。長鋪王家有一人在縣團防局當差�����,回家來在街上喝酒���,說了句“終究成不了氣候”的話,被隔墻有耳聽去�����。不久���,那人再回家���,被土匪盯上,趁夜綁了����,押往訇訇巖��。從長鋪街上過��,驚怖異常地喊����,“地方人救命�����!地方人救命���!地方人做主!做主啊���?��!卑肜锫烽L,沒有一丈寬的長鋪街���,沒有一扇鋪門打開����,沒有一個人吭聲。從街頭喊到街尾�,最后有一人開門來想求情,被土匪當即拉上����,“汗!【發(fā)語詞】港公道���?你也算一個�����!”深更半夜兩人被推下三十丈深的訇訇巖底���。訇訇巖?扔顆石子下去����,好久還聽到“訇訇”聲經(jīng)久不息的。
長鋪里的釘心話和周家人的椏扎話�,就如此在照面山的溫潤和險惡中生成。
照面山的山溪水滋養(yǎng)了山下肥沃的土地��。在武岡南鄉(xiāng)安心觀,照面山的水從九嶺十八溝流下來��,性子之急�,也比作長鋪里話的陡寸和椏扎:“你怕是吃了照面山水?”
“酒是癲狂之藥�!”椏扎話如果像酒,也算是醇和的酒����。而釘心話,則要濃烈得多��!
2015年8月20日于武岡

都梁記憶:本名黃家冰����,字水平���,男���,現(xiàn)年53歲,武岡南鄉(xiāng)安心觀【文坪鎮(zhèn)】人��。武岡一中高中肄業(yè)�。命相學斷為火命,所以名字里有冰和水。
人生感言——感謝這火命�����,燃燒了多余能量��,才沒有能力干更大的好事或者壞事��!